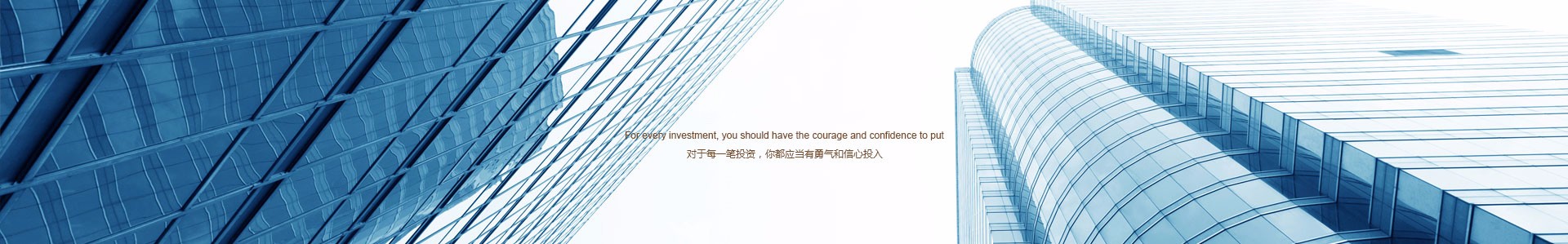凤凰体育- 凤凰体育直播- APP一代官商的全球化末路
2025-09-20凤凰体育,凤凰体育直播,凤凰体育APP

按道理,他跟英国关系更深,合作时间也更长,从东印度公司到怡和洋行,从茶叶贸易到贸易,一直都在合作,但他还是看好后来的美国,他从美国人的眼里,看到了善意。
不光从美国小子福布斯眼里,还从旗昌洋行美国商人的眼神里,他都看出了善意,并从中感受到“美国的善意”。
“美国的善意”,主要表现在对“中国旧制度”的宽容和理解,并从中吸取一些好的东西,他们吸取了哪些好东西呢?胡文辉在《中国旧制度影响美国的几条线世纪,中国作为“繁盛的古典文明”,曾通过制度创新,间接塑造了美国的某些现代制度。主要通过“三条路径”实现,其中有一条,就与清代广州十三行的“保商”制度有关。
所谓“保商”,即由官方授权外贸,以行商承担约束外商、上缴关税责任,各行商之间,还负有连带责任,若一行倒闭,所有行商都要分担其债务。这种债权担保制度,成为1829年,美国纽约设立“安全基金”的样板,而此“基金”,是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存款保险计划之一,也是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雏形。
在荷兰汉学家包乐史(LeonardBlussé)《看得见的城市: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浮沉录》中,可见当时“安全基金”倡导者佛门(JoshuaForman)写信给纽约州长说明:在那里,一群各自行动的人,在政府的允准下,拥有与外国人交易的排他性权利,当彼此生意失败时,其债务是可依赖的,此原则已历70年考验,获得了全世界的信任,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可以超越它。将此原则调整并使其适应我们共和体制的温和特质,就成了这个系统的基础。
在这里,佛门说得很明白,美国的“安全基金”,是以十三行的“保商”制度原则为原型,加以“调整并使其适应我们共和体制的温和特质”,也就是在“保商”制度的框架内,注入了“共和体制”的法的精神,因而表现出了“温和特质”,改变了原来制度安排里的治理逻辑,以实用主义的方式,借用其工具理性。
从根本上来说,清代广州十三行“保商”制度,是清政府为管控对外贸易而设计的重要机制,其形成与演变,反映了清朝“以官制商,以商制夷”的治理逻辑,其制度起源,可谓保甲制向贸易管控延伸,“保商”制度与“公行”组织,相辅相成。
“公行”组织成立于康熙五十九年(1720年),由官方授权行商组成,垄断对外贸易。“保商”制度,出现在清乾隆十年(1745年),清政府首次规定,所有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,须由指定行商担任“保商”,担保外商缴纳税款等。这一制度,借鉴了原有的保甲制度,将行商群体纳入官方管控体系,形成“行商互保、一商亏折全体连带”的责任链条,乾隆十九年(1754年),为强化“保商”制度,明确行商之间承担无限连带责任。故其于制度运作方面,表现为双重角色,既是外商法律担保人,也是贸易中间人,对外商税款缴纳、行为规范负有全责,若外商违约,“保商”需承担罚款、甚至“封舱”的后果。同时,保商享有优先购销外商货物的特权,成为贸易利益的既得者。
初期,“保商”由官方轮派,被外商后有所调整,改为由外商自选,报官方认可。道光十五年(1835年),增设“派保”一职,由行商轮替,监督自选行为,故外商常以“限制自由”为由,反对“保商”制度,但清政府仍以“封舱”强推。其政治意图,是采取“以商制夷”的治理逻辑,通过权力渗透与利益捆绑,“保商”制度将行商作为管控外商的工具,既避免直接与外国势力冲突,又确保税收和主权象征的维护。
“保商”制度的本质,是形成官商利益共同体,行商通过垄断贸易,获取暴利,而清政府则通过行商缴纳的“行佣”——贸易抽成和巨额捐输——如战争赔款、赈灾捐款等充实财政。据统计,1773-1835年间,十三行累计捐银达460万两。
“保商”制度最终随《南京条约》的签订(1842年)而废除,其崩溃的直接原因,是五口通商打破了广州的贸易垄断,深层原因则在于制度本身的矛盾。首先因为经济压力,行商因“商欠”债务连带而频繁破产,如潘家曾因外商违约被罚12万两;其次外交失能,面对西方列强,“保商”制度无法适应新的国际法。
作为“保商”制度里的核心人物,伍秉鉴当然理解美国“安全基金”的好处,因为,这是他投资美国最先要考虑的,其投资“安不安全”,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这个“安全基金”。
由于该“基金”吸收了十三行“保商”制度的风险管理的精华,并剔除其制度腐败的糟粕,故其尚能于“知根知底”处,知晓其要略,执得其要领,且对此“基金”的认知中,多少能看到一些“自我”的影子,使他能深刻的感受到“美国的善意”。
除了中国之外,这个世界如果还有个能够为他留后路的地方,那就只有美国了。不光因为他收了个美国义子福布斯,还因为美国有个能与他相通的“安全基金”可作为其财富信托。那么,那个与他交往甚深且一直由他来担保的英国呢?他看出来了,那不是给他留后路,而是要断他后路的地方。
伍秉鉴知道,英国人看不上十三行,他们早已不满足于一口通商,只是迫不得已才接受了清廷的“保商”,屈尊来跟他合作。从本质上来讲,英国人否定了十三行,只待有朝一日能给它致命的一击。而这一击,不但会断他财路,还会要他命。
在朝廷和英国人之间,他是中间人,本来代表朝廷跟英国人做生意,但朝廷不给他俸禄,只给他授权,还要他来作担保,为来自遥远异国的商人做担保,这等于将他的身家性命都押给了外商,外商若是违约,或为诈骗,都有可能使他致命。而他却只能从外商那里获利,故其作为当时最大的外商——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担保人,即与之深度绑定,以预防不测。
为此,他成为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“最大债权人”,那时,能作为全球化程度最高且代表日不落帝国国家信用的东印度公司的“最大债权人”,即便放到世界历史上,那也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,若放到中国历史上,就更是明清两朝的高光时刻了,可以说是全球化绽放的白银之花结出的时代硕果。然而,这一硕果怎么看,都是东西方时来运转中碰撞出来的一个财富奇葩。
若放在他本人的头上,往好处说,他是十三行的幸运儿。说伤心处,他又是“保商”制度的产物,人为其“刀俎”,他却成为“鱼肉”。其财富生态,介于两个对立的共同体之间,一个是本土化的官商利益共同体,还有一个国际化的“洋商-行商”利益共同体。好运来时,他长袖善舞,执两用中,左右逢源,维持着两个利益共同体的平衡;运气不好,则被左右夹击,将其撕裂。两个共同体的合力,可以将他推上世界首富,也能使之成为人间妖孽。
若非深度套牢,焉能宿命于此?在官场上,他原本捐了个三品顶戴,但说摘就被摘。在官本位的天下里,花钱买官,无非想买个身份,买点尊严,可结果买来的,却是无穷无尽的羞辱和勒索。身份成为他的一个枷锁,可以用来名正言顺地绑架他自己,令其无法摆脱。
官场如此,市场方面又如何呢?为了财富增长,更为了身家性命安全,他又投资了英国东印度公司,非以股权方式,而以债权方式,成为了当时最大跨国公司的“最大的债权人”。
仅凭这一点,他就无愧于“世界首富”这个银光闪闪的头衔,说得好听点,他成为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值得信赖的“银行家”,若换个说法,他又何尝不是这家公司取之不尽的“提款机”呢?其中“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”的紧张滋味,揪着他的心扉。从表面看,该公司因问题,常向伍家借贷,但实质上并不那么简单。不但表现为贸易双方的利害博弈,还有可能转化为国与国的商战,伍家为什么要参与其贸易?其主要原因还不是要获取暴利,而是向该公司交纳投名状,成为其真正的“合伙人”。
伍家这样做,是出于“保商”本能。在清朝的“保商”制度下,作为“保商”的伍家,被两头拿捏:一头被清政府拿捏,另一头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拿捏。政府只管拿好处,让“保商”不但为自己的国家做担保,还要为他无法担保的外商担保,而国家却从来不为“保商”担保,这就等于将“保商”推入外商的怀抱,尤其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那样的外商,伍家惟有投入。
投入有投入的好处,若无投入,伍家如何能成为“世界首富”?然而,“首富”如何炼成,要熔冶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于一炉,其“天时”者何?白银时代也;其“地利”者何?“天工开物”之中国是也;其“人和”者何?全球化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也。
可以说,伍秉鉴作为“世界首富”,是在白银时代由中英两国共同打造出来的,由中国提供世界上最大的手工业生产的制造业基地,而英国则将其导入一个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际市场。“伍怡和”作为国际品牌风靡全球,就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成就的,连承载马戛尔尼一行来到中国的商船,也由伍家来担保。
中英两国合作的这股作用力,举之,可将其送上财富的云端,而其代价便是,既要维持“天子南库”财源茂盛,又必须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“最大债权人”(实为“提款机”),当两者不可兼得,其相互排斥的反作用力也巨大;抑之,也可将其打入地狱。这一关系,既体现了全球化初期以伍家为代表的中国商人的资本实力,也揭示了官商体制与殖民资本夹击下中国商业资本的脆弱。
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“最大债权人”,怡和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了长期的信贷关系,其借贷规模虽无明确统计,但据多方史料及商业背景可推测其大致投入的白银数额。
虽具体单次借贷数额未直接记载,但综合其贸易规模来看,19世纪初,伍家与东印度公司年贸易额已达“数百万两白银”,其中有一部分可能转化为信贷资金,若以占其总资产的10%-20%的比例来推断,伍家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放贷总额或达数百万两,应不低于它在美国的投资,方可称之为“最大债权人”。
如果说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在东方的“提款机”,那么,伍家就是东印度公司通过贸易在中国的特别“提款机”。
其“提款”的大头当然是印度,英国政府通过公司间接征税,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以包税制,将搜刮的财富层层上交。仅1757-1815年间,英国从印度掠夺的财富就高达10亿英镑,其中,每年约1000万两白银以税款形式汇回英国,成为英国政府的一项财源。至19世纪末,英属印度年净收入达4400万英镑,又有1600万英镑以税款形式直接用以支持英国财政。
而“提款”的头寸也不小,且有后来居上的架势。通过走私,在1807-1839年间,中国净流出白银超1亿银元,不但一举扭转英国贸易逆差,而且利润成为了英国殖民经济的支柱。
伍秉鉴家族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“最大债权人”,在“提款”中的分量不容小视。此举或与伍家意愿无干,但与英国“以债养战”的国策有关,当年英国就借荷兰人的钱打败了荷兰,很有可能,伍家就是英国人针对中国如法炮制的一个对象,借中国人的钱搞贸易以削弱中国,以战争击败中国。
东印度公司实为英国政府的白手套,但凡政府不能出面干的脏活,都由它来代理,采取公司取代国家的殖民模式。
乍看起来,印度殖民化并非由英国政府主导,而是由一个注册在伦敦金融城办公室操控的私营企业来完成的,然其本质,就是一个“伪装成商人的帝国”,凭借英国王室授予其特许状——允许开战、征税、统治领土,能以军事征服与商业垄断相结合。
自1600年伊丽莎白一世授予其贸易垄断权后,该公司通过军事征服(如1757年普拉西战役)、金融操控(如1765年获得孟加拉征税权)的代理人渗透,逐步瓦解莫卧儿帝国,最终以企业身份完成了对印度的殖民化。到1803年,其拥兵20万,超过英国陆军两倍,实际统治500万平方公里土地。公司还通过扶植傀儡统治者,对其殖民地所属国实施系统性劫掠,如1757-1765年从孟加拉攫取3700万英镑财富,实现了“资本驱动的领土扩张”。
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双管齐下,构建了一个“强制私有化”的企业殖民范式,其使命并非“传播现代性”,而是以“企业绑架国家”来行使其统治,视印度为“资本增殖的原料”。为求得公司利润最大化而导致的“孟加拉大饥荒”,饿死了1000万人。
随着公司腐败和财政危机频发,如1772年金融危机,1773年英国政府通过《调整法案》,1784年又通过《印度法案》,逐步接管了公司控制权。法案规定,公司需向财政部提交财务报告,并由国王任命印度总督,实际上是将印度事务纳入政府管理。印度总督虽由公司董事会提名,但需经国王批准,并对议会负责。
这就使得公司高管通过殖民掠夺积累财富后,得以回国进入议会或政府,形成其“黑金政治”网络。例如公司核心人物克莱武等,以其压倒一切的财富能够左右英国政局,前首相皮特曾批评这些人“凭借腐败横行闯入议会”。这种利益交换,使得政府长期默许公司的暴行,甚至为其暴行提供军事支持。当其因扩张而濒临破产时,如1772年欠债900万英镑,英国政府通过英格兰银行提供140万英镑贷款,这是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政府救市行为。作为交换条件,公司需接受《调整法案》,将印度治理权移交政府,使殖民事务从商业行为转为国家行为。
为缓解其财政压力,英国政府授予东印度公司北美茶叶专卖权,但此举又在1773年引发了一场“波士顿倾茶事件”,以此导致了美国的独立战争。英国这一政策,暴露了政府与公司利益的高度绑定,以及为维护垄断不惜激化殖民地矛盾的本质。
工业革命后,东印度公司将印度变为英国纺织业的棉花原料产地,1794-1813年,英国输印纺织品增长700倍,摧毁了印度国产纺织业,使得公司收入与英国工业资本利益深度捆绑。为了平衡对华贸易逆差,英国政府默许该公司在印度种植,并走私至中国。战争后,该公司通过《南京条约》获得巨额赔款,其中部分款项,被用于填补英国政府财政缺口。
对于这一切,伍秉鉴知否?当然无知,若有知,也是知之甚少。他哪里能知道东印度公司在被英国政府吃干用尽之后即将被抛弃呢?他哪里会知道英国政府为了国家安全正在收紧风险准备“金蝉脱壳”呢?在战争即将到来之时,他作为该公司的“最大债权人”,也混在同一盆全球化的脏水里,被英国政府一起倒掉了。